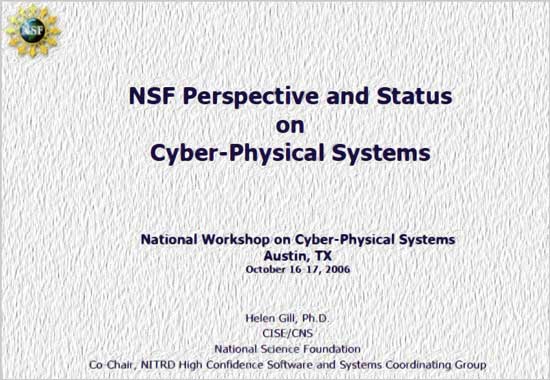最近在上海工业4.0俱乐部做了一场演讲,题目是《资本市场强国背景下的中国制造》,主要谈到了我国新提出的“资本市场强国”和中国制造2025的四大流派。前者是中国证监会提出的新名词,后者是工业4.0研究院在2017年研究的新成果。
记得2015年,同样在上海,我在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做了两场演讲,分别是《工业4.0之中国挑战与机遇》和《工业4.0时代的资本秘密》,主要阐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些规律。

在2018年,我再次拜访上海,具有不同的意义,因为工业4.0研究院已经与国家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,并且帮助一些上市公司设计和实施了工业4.0战略,有了一些新体会,所以在工业4.0俱乐部的年会上跟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进行分享。
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资本家
在我跟工业4.0俱乐部的行业人士分享了《资本市场强国背景下的中国制造》之后,有大量的企业家和投资基金跟我私下交流。一方面他们为我再次阐述“技术+资本”的理念表示赞赏;另外一方面,他们提出了一个疑问,既然我提出了新资本家的说法,但怎样才可以成为新资本家呢?
要认识工业4.0时代的新资本家,必须要先认识到工业1.0、2.0和3.0的资本形态之间的不同。
首先,工业1.0是资本主义的雏形,工厂还没有形成高度专业分工的流水线生产,这个时候的工厂投资并不大,因此,工业1.0阶段的资本来源主要是家人、朋友或同学等,没有专业的资本家。
其次,在工业2.0形成的流水线,大大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发展,这迫切需要更大规模的资本投入,按照一些文献的说法,仅仅通过传统的银行借贷方式,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,开始出现了一些专业的投资银行,例如,摩根大通等机构,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。
再次,到了工业3.0,也就是所谓数字时代或信息时代,大量的无形资产开始出现,这些无形资产是难以被传统的投资银行所评估,但要创造这些无形资产(很多时候是数字资产),需要的投资一点都不比传统物理资产少,这迫使一些懂专业和敢冒险的天使投资、风险投资(VC,Venture Capital)、私募股权(PE,Private Equity)等出现。
最后,我们来看看工业4.0时代的新资本家。按照工业4.0研究院的理解,新资本家应该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:
一是具有专业性,通常要介入到特定的领域去投资,如果对该领域理解不够深入,是很难进行专业判断的。
二是需要在不同阶段进行投资,主要是按照TRL 1-9所划分的三个阶段,按照不同的着力程度,形成了不同的风格,例如,知名的人工智能专家吴恩达(Andrew Ng)最近设立了AI Fund,他把重点放到TRL 1-3,这跟传统投资基金做法是不同的。
三是生态投资开始成为标配。在中国国内,有些投资基金希望找到一些投资风险小、回报高的项目,但由于投资基金数量增长非常快,基本上呈现了过剩的状况,要获得较好的回报,必须提高投资的效率,生态投资是较好的选择。
中国制造2025的四大流派
回顾中国制造业在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,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时间,中国制造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,随即中国制造开启了多轮探索强国之路的尝试。
2015年,国务院发布《中国制造2025》,明确了多个关键概念,例如,两化融合的主线,智能制造的主攻方向等。后来,随着2017年底把工业互联网确定为中国制造2025的主攻方向之一,工业互联网也成为了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词汇。当然,后来我国进一步加强“新一代人工智能”的发展,促进了中国工程院提出了“新一代智能制造”。
除了前面提到的官方体制内单位提出的概念,一些企业或独立机构也提出了一些说法,例如,海尔和红领共同提出了“互联网工业”,华为提出了“边缘计算”,中国互联网协会提出“产业互联网”,阿里研究院过去几年重点关注了C2B等概念。

按照工业4.0研究院设计的流派判定三大基本要素,中国制造2025可以分为四大主流流派,分别是两化融合、智能制造、工业互联网和智能服务流派。
工业4.0研究院认为,一个主流的流派,应该满足三个要求:
- 有较强的研究能力,具有不断完善范式和体系的能力,可以吸纳新出现的各种优秀元素(例如人工智能、数字孪生体等等)。
- 具有包容性(inclusive)的理念,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技术路径、实践方法等,可以被较多的利益相关者接受。
- 可以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,通常情况下,具有生态特征的概念流派更具有竞争力。
在中国现实情况下,获得各个部委的支持,更容易推进相关概念和体系。两化融合主要是工信部一所在推进,已经有十年左右的时间,也是工信部的立部之本,自然是主流流派之一。智能制造涉及到工厂现场的流水线,装备决定了生产的效率和效果,目前主要是中国工程院在负责相关理论体系构建,无疑也是主流流派之一。对于工业互联网,这毫无疑问对应到“网络强国”的需求上,工信部信通院负责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的运行,也应该是主流流派之一。对于最后一个智能服务,实则是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成果,虽然目前还没有公认的领头羊,但考虑到大数据、人工智能和互联网+的应用,该领域也应该是主流流派之一。
对于其他非主流概念,大都是单个企业(通常也是比较大型的企业)在推进,或者是该企业利用产业链上的主导地位,联合自己的供应链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组建的联盟推进,通常不满足上面提及的流派判定三大基本要素,所以也不详细介绍。
总而言之,在资本市场强国牵引下的中国制造2025,目前主要呈现四大流派百花齐放的场景,这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毫无疑问是有益的。除了四大主流流派,其他概念和体系,也将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其作用。